秋天来了,我想随风远去,可我哪儿都没去
“城市的黎明降临了,在灰蒙蒙的天色中,一群人等着早班公交车的到来。这时候,整夜都没睡觉的人需要吃些热的东西;睡梦中的人在被子里寻找彼此的手,而他们的梦境变得更加清晰;报纸散发出墨香味,白天发出第一声喧嚣。”
意大利小说《虚掷的夏日》描绘了这样一场浪漫感伤的罗马citywalk。这部一度消失的经典是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欧洲文学遗珠。
都市生活虚浮迷惘,而在年轻漫步者必然失败的命运中,却蕴含着一种令人深陷其中的自由之感。
下文摘选自詹弗兰科·卡利加里奇《虚掷的夏日》,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阿丽安娜对夜晚了如指掌。
十五分钟后,我们推开了一家面包店的门,那家店藏在法院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我们进入了一间洁白的地狱,到处都是面粉和正在干活儿的人。
有些人揉着松软的大面团,在桌上拍打,就好像在惩罚它们,让它们变得温顺;有人则将面团切成小块,把它们放进烤炉里。还有几个裹着白色头巾的女人,她们在装满馅料的容器里搅拌着。
“啊,你来了,公主。”她们中的一个说,“今晚你想来点什么?”在那女人慈爱的目光中,阿丽安娜指了指各种馅料的牛角酥。那女人装了满满一个纸袋。
阿丽安娜用两只手捧着纸袋,牛角酥热乎乎的,闻起来香喷喷,但她在离开之前还偷了一块玛德琳蛋糕。

我对那位女士说晚安,阿丽安娜用手肘撞了我一下。“说什么晚安!”在院子里,她对我说,“他们已经干了几个小时的活儿!”
她叹了口气,说:“每次来这儿,我都会有很强烈的负罪感,但为了吃上这些热腾腾的牛角酥,我什么都顾不上了。你不这么觉得吗?”
牛角酥热乎乎、香喷喷的,和一般餐吧里那些让人悲哀的小蛋糕截然不同。再过几个小时,城里那些小职员就会去那儿,用小蛋糕蘸着卡布奇诺吃。
“不用还房贷,还是有些好处。”我说。
但阿丽安娜完全没听我说话,她专心咀嚼着玛德琳蛋糕,脚在院子里的鹅卵石上探索。“你在找一块裂开的地砖吗?”我问她。
我对普鲁斯特典故的卖弄戳中了她。“那也没什么用,”她好奇地打量着我,说,“它们不再是之前的玛德琳蛋糕了。”
“没什么会一成不变。”
“这个开头不错,”她说,“继续说下去。”
“是啊。”我说,“正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哀的时代,那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别无选择。”
“的确,”她忍住笑说,“我们别无选择。你有没有想过,社会发展夺走了我们多少快乐?”
“怎么没想过。比如说,喝玻璃瓶装的牛奶。”
“是的。”她说,“说得对,还有呢?”
我说,在翻阅图书时不用撕去书上的塑封;她说,那时可以用纸袋子玩爆破游戏。我说,以前大家都是手工切火腿,现在都是机器切;她说,以前大家都穿胶底鞋,圣诞树上的玻璃装饰品可以摔碎来玩。我说,以前皮沙发的味道很好闻;她说不出其他的来,就转移了话题。
“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出生在什么时候?”
“奥匈帝国灭亡前的维也纳?”我说。
“不错的选择。”她边说边坐上车,“我想出生在法国贡布雷小镇。你来开车行吗?我想从卡比托利欧广场的观景台看这座城市。”
五分钟内我们就到了那里,靠在古罗马广场遗址正上方的栏杆上。我们下面是空荡荡的广场,大理石建造的神庙歪斜着,仿佛正在梦想有一天能重回荣光。
“真愚蠢!”阿丽安娜轻声说。
“你指什么?”
“留恋过去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她转过身,看着几个在长椅上睡觉的流浪汉,这时她刚好看到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正符合她的游戏。
“其实,我很羡慕他们,” 她说,“他们很自然地融入了这个世界。你是做什么的?”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她,我什么也不做。
“怎么可能什么也不做?”她说,“每个人都有事做。我也有事做,虽然看起来并不像,但我是学建筑的,学习期满了,还没拿到学位证。那你每天都怎么度日?”
“读书。”
“你读什么?”
“什么都读。”
“你说什么都读,那你也会读电车票、矿泉水标签,还有市长发布的清理积雪的通知吗?”她大笑。
“是的,但我更喜欢读爱情故事。”我说。她信了我的话,说她觉得那些爱情故事都很让人绝望,因为她喜欢的故事结局都很悲惨;但结局悲惨的故事她又不喜欢。

她问我有没有看过《追忆似水年华》。“我气短,读不了这个。” 我说,同时我声称,普鲁斯特是要大声朗读的作家。这一观点引起了阿丽安娜的兴趣,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作品需要大声朗读。我提到了一些当时想到的书:《圣经》《白鲸》《一千零一夜》。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书。
“你也是有偏好的。”
“的确,”我说,“亨利·詹姆斯·乔伊斯,鲍勃·迪伦·托马斯,斯考奇·菲茨杰拉德,通常来说都是旧书。”
“为什么是旧书?”她问,并没领会到我用作家名字玩的文字游戏。
“因为便宜,而且这些书已经有人读过了,有一定的质量保障。你能事先知道它们是否值得一读。”
“怎么才能知道?”她坐在矮墙上说。我说,我会在书里找面包留下的痕迹,比如面包屑、面包渣什么的,因为要是一个人边吃东西边看书,那这书一定很不错。或者我会在书页上找油渍、指印,还有折痕。
“折痕需要在切口上找,人们看一本书时会折页,说明这本书也值得一读。如果是精装书,我会在封面上找污渍、擦痕或划痕,这都是可靠的证据。”我说。
“如果之前看那本书的人是个笨蛋呢?”
“这样的话,你得多少了解一下作者。”我回答道。
我继续说,电视出现之后,阅读正成为一种过时的活动,只有那些相对聪明的人还在坚持阅读。
“读者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群体,就像鲸鱼、山鹑还有其他野生动物。”我说, “博尔赫斯称他们为黑天鹅,他声称,好读者比好作家更为稀缺。他说,不管怎样,阅读出现于写作之后,它更顺从、更文明、更智慧,不是吗?”
我继续说:“阅读的时候,你会面临另一种风险。你读书时心境不同,书给你留下的印象也会不同。一本书,你第一次读时觉得它平平无奇,第二次读却会感到震惊,只因为在此期间你经历了伤痛,有过一次旅行,或者你恋爱了。总之,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任何意外发生的事情,都会改变你对那本书的看法。”
02
好了,现在她知道了,她面前的人有多么心高气傲。她默默地听我说着,眼睛一直盯着花园里潮湿的鹅卵石。她抬起头。“你很有趣。”她说,“你知道吗,当你走进维奥拉家时,看起来很悲惨。”
“我只是饿了。”
“饿?”
“是的,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字吗?”
“怎么会?”我们走向汽车,她笑着说,“那不是人们喝开胃酒时会产生的感受吗?”她走到汽车旁边,坐到发动机盖子上,环顾四周。“住在这儿,应该会很有意思。” 她说,“但我不愿意嫁给市长。”

“你住在哪儿?”
“紫藤街,”她兴致勃勃地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在梧桐大道那边。”
“对,附近有一条我很喜欢的街,叫丁香街,还有一条街叫兰花街。”她说出那些花的名字,就好像那些街道是用花铺成的。“你送我回家吧。”她说着,把方向盘让给了我。
“说真的,你到底住在哪儿?”我说,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住在那种地方。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将雨靴搭在挡风玻璃上。
我已经到了极限,精疲力竭,但我想知道,她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开着车,去了那个叫紫藤街的贫民窟。
我受不了那地方,整个街区道路混乱,有很多趟电车经过,是我见过的最破烂的电车。刚建成的房子摇摇欲坠,发臭的小饭馆旁边是电器店或修车铺。
成群的孩子骑着吵死人的摩托车,改装过的发动机发出地狱般的噪音。人行道上弥漫着从电影院涌出的消毒水的臭味,简直能把人熏死。整个城区没有一座花园、一棵树或一个花坛,可以让居民在夏天躲避一下太阳的暴晒。
因此,马路拐角处路牌上那些花的名字,让人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疯子的梦里。
像她这样的姑娘去那儿做什么?我没再说什么,把车子开向路灯昏暗的郊区。路两边是蜂房一样的居民楼,像高耸的墓地。阿丽安娜用她的大眼睛看着外面,没有出声。
我们经过一个破旧的露天游乐场和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围墙,汽车的影子映在几家电器店的玻璃橱窗里。我们在青灰色的天色中向前开,终于找到了紫藤街。
这条街道很窄,上方挂满了晾着的衣服。我们到了目的地,除此之外,这儿只有废墟和荒凉。“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她说,“你完全搞错了,这不是我说的紫藤街。”
“没有别的紫藤街了。”
“当然有。”她说。她迅速拿出香水,把香水喷到手腕和额角上。丁香花的味道弥漫在车厢里,事实上,香气让这街道的景象变得可以忍受。
一个穿黑衣服的夜间巡逻队员单手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来。
“快走,求你了!”她说,声音很痛苦,“我很怕那些夜间巡逻队员。”
她抓住我的手,用力握着,直到我们离开了那个街区。实际上,她不仅没在紫藤街住过,也从来没去过那里。
她说,那天早上,她看到了一条广告,出租两个房间。那些以花命名的街道让她以为那里是一个住宅区。在城市地图上,那个街区有点偏远,但她怎么能想到,那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地方呢?唉,那地方真糟糕!
我没说话。她之前应该是太寄希望于那些花的名字了。但我想知道她在逃避谁,毫无疑问:她离家出走了。
我在想,她离开了谁。后来我知道,她躲的是她姐姐。那天早上她们吵架了。尽管对她来说,独自生活真的很恐怖,她还是决定离家出走。

我问,她走的时候,只带了一本普鲁斯特的书、几根火柴和一瓶香水吗?“还有一副纸牌。”她自负地说,“不可以吗?”
她去任何地方都带着一副纸牌,只不过在和姐姐吵架的时候,她忘了带钥匙,被锁在了外面。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些熟悉。
我正想着在那个倒霉的雨天,一大早出来就淋了雨,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我忘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是忘记了:在生日的那天,我一整天都在试图回想起那天是我的生日。
“什么?你居然忘了你的生日?”
“没错,”我说,“生日也再不像从前一样了。”但我想起来,我之前答应自己,从那天起我要开始做的所有事。我看着天空,好像人们年满三十岁时,总是要看着天空。
“你一定是疯了。” 阿丽安娜说,“一个人怎么能忘了自己的生日呢?离生日还有一个月,我就会开始在日历上做标记!”面对如此特别的情况,她忘记了紫藤街,还有其他事。
“我们也要庆祝一下。”她说,“我们找一家咖啡馆吧。”
03
在找咖啡馆时,城市的黎明降临了,在灰蒙蒙的天色中,一群人等着早班公交车到来。
这时候,整夜都没睡觉的人需要吃些热的东西;这时候,睡梦中的人在被子里寻找彼此的手,而他们的梦境变得更加清晰;这时候,报纸散发出墨香味,白天发出第一声喧嚣。
天亮了,夜晚给我身边那个奇怪的女孩留下了两个黑眼圈。
“为了所有我们没做过的事,为了那些我们本应该做的事,也为了那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干杯!”我一边说,一边举起满满一杯热腾腾的牛奶咖啡。阿丽安娜笑了起来,说她感觉这像一句祝酒词,太正经了,但其实也可以。

她身子向前探过来,越过咖啡桌在我脸上吻了一下。“现在,” 她坐在金属椅子上说,“给我讲些有趣的事。”
我们身处公交车终点站的一家咖啡馆,周围满是咖啡的香味,那是咖啡馆清晨会散发的味道。几个司机正站在桌前读《体育邮报》,一个伙计把木屑撒在了他们脚边的地板上。
喝完一杯牛奶咖啡后,我感觉很好,虽然浑身的骨头有点疼。我告诉了她我从前在紫藤街的遭遇。那段时间,我给一群小孩上语文课,但那些小孩更喜欢把我口袋里的烟偷走,而不是去思考《约婚夫妇》为何有别于一场迟来的性交。
最后一节课我本来要讲虚拟式,但我连续三天都喝醉了,椅子都坐不住。他们注意到了,开始轻拍我的肩膀,而我为了得体一点,假装这样很好玩。
但我最后没坚持住,突然瘫倒在地板上。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学生的父亲把我横放在一辆摩托车上,送回了旅馆,我就像一个死掉的印第安人。
我不记得是不是这样,但我知道,我清醒时上课的费用,他们也没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筹划着绑架其中一个小孩,来索要赎金。
阿丽安娜笑了起来,但又突然停下,从杯子上面观察我。她眯着眼睛,仔细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我喜欢你灰色的眼睛,在想,我会不会爱上你。”
“没这个必要。”我说。我想点一支烟,但没注意到点燃的是有滤芯的一头。“只要你愿意,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来我家,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真的吗?”她问。我的话让她很振奋,她马上说,她不会给我添一点麻烦,我们将分摊房租,因为她每月有五万里拉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也够生活。而且她会做夏多布里昂牛排,味道超级棒。
这时我想装腔作势一下,说她不用做夏多布里昂牛排,因为这让我想起了那位因牛排而被载入史册的诗人,这会让我觉得悲哀。她说,如果我更喜欢政治家,那我们就吃俾斯麦牛排。
她想聊聊我们怎么打发日子,我们会看书、听音乐、学习。她必须重新开始学习,拿到那个该死的大学文凭,才能回到威尼斯,成为某个技术小组的成员,去拯救那座城市。唉,只是她一直都无法专心学习,她太没有条理了,脑子太乱了!几点了?尽管她手腕上戴着一块沉甸甸的男士手表,她还是在问时间。
嗯,这块表?祖传的手表。时间不准,而她也从不去校正,这样看钟点时,总会有惊喜。
六点了,手表的指针却指着七点四十五,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04
“我马上回来。”她说着,起身去了洗手间。洗手间的门关着,她得去问服务员拿钥匙。她回来时一脸嫌弃。“他们把门关上,可能是害怕有人进去替他们打扫吧,”她说,“现在我们做什么?”
“我们回家,怎么样?”我说。
我很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阿丽安娜摇了摇头,在抽了一晚上的烟之后,最好还是去海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这真是个好主意,我怎么会不赞同呢?我在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东西可以击垮她,击垮她,以及她的脆弱。
她开着车在大路上疾驶,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开上了通往海滨的路。路边的草地上满是露珠,在明净天空的衬托下,松树现出黑色的轮廓,这时,天空的颜色正在发生变化。
阿丽安娜像是有点神志不清,她说起我们将要一起度过的日子。而我对着天空闭上眼睛,听着她的声音,想象着这声音回荡在山谷上空荡荡的房子里,会是什么景象。啊,这世界还有救!
大海忽然出现在道路尽头。我们开始沿着海岸线行驶,大海在公共浴场之间时隐时现。左边是淡季的民宿和小旅馆,清新又强劲的风吹动花园里的棕榈树,露出褪色的招牌。
四周很寂静,阿丽安娜这时也不作声。我们把车停在一片居民区外的路边。天空正变成粉红色,但大海还是铁青色,好像满怀敌意。“它好像在要求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但水就是这样。雨好像也总是在要求什么。”
我们走上沙滩,风吹透了衣服,带走了刚才在车里积攒的热度。
她瑟瑟发抖。“好冷。”她说,“冷死了!”她在潮湿的沙子上跑起来,手插在红雨衣的口袋里。
不一会儿,她就跑到很远的地方了,而我在沙滩上坚硬的地方走着,脚下是一层干巴巴的海藻和空贝壳。
海水轻轻拍打着我的鞋,在回头浪的冲击下,一点点向前推进。我看向她,红色的雨衣让她看起来像一个木偶。风吹着雨衣,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把脚踩在她留下的脚印里,跟着她的足迹走。
风玩了一个奇怪的游戏,我赶上阿丽安娜时,她在晨光照耀下转过漂亮的脸庞。这时候风停了,仿佛为了喘一口气,接着又开始吹起来。她抬起手臂,环抱着我的脖子时,红色雨衣又发出一阵沙沙的声音。
她冰冷的袖子贴着我,我突然哆嗦起来。“你冷吗?”她说,用她那僵硬、娇小但又温热的身体搂紧了我。
她轻笑起来,呼吸钻进了我的衬衣领口,我感到她的嘴唇在我脸颊上轻轻移动。
“小可怜……小可怜……小可怜……”她轻声打趣着我,“我对你做了什么……小可怜……”直到她的嘴唇越来越轻盈,微笑也消失了。她的嘴唇印在我的嘴唇上,她的舌头温柔又固执,想要开启我的牙齿。
然后她缓慢地离开了,那感觉难以形容。她的动作从始至终都很缓慢,最后她在我雨衣的翻领上蹭了蹭嘴唇。“我说!”她大笑着说,“你该不会想做爱吧!我真不喜欢你的想法。”
她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
她走近一小群渔民,他们正在往岸上拽一张网,网已经出现在水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收获不多。渔民在小声咒骂,这时天空正从粉色变为蓝色。

“看!”阿丽安娜大喊,“你快看!”我看见,魔法正在改变这个早晨。一个老人在沙滩上散步,每次他快要跌倒时,都会举起他的拐杖,驱赶一条肮脏又好斗的断尾狗。
阿丽安娜松开了拳头,她的手已经抓握了四个小时。“真可笑。”我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还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太笨拙了:我试图抓住她的手,但她把手插进了雨衣口袋里。
本文摘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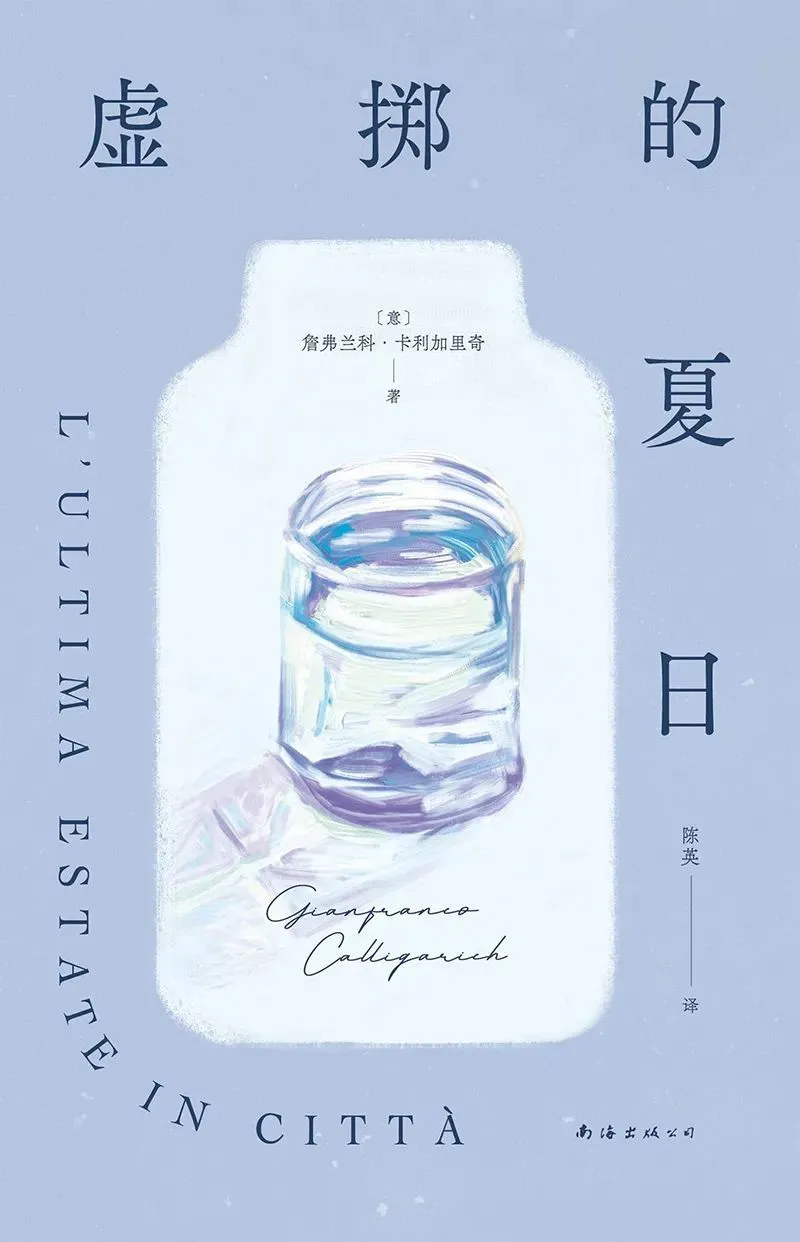
《虚掷的夏日》
作者: [意]詹弗兰科·卡利加里奇
译者: 陈英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 20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