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吃好一碗豌杂面 陈晓卿
美食的终极意义在于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幸福感
陈晓卿说:“。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有时候和食物本身相关,有时候和生活经历相关,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
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
作为《舌尖上的中国》和《风味人间》的总导演,陈晓卿是个不折不扣的“国民饭搭子”。读他的美食随笔,好像能跟着他吃得更香、吃得更美,又能随他看见食物承载的记忆、食物传递的情感。毕竟。
如何吃好一碗豌杂面
工作地点的变更,让我很确切地感受到了北京城市发展的不均衡,饮食方面尤其如此。
从前在CBD上班,隔三岔五总会和同事一起以光华路为X轴,大望路为Y轴,不出十分钟,总能找到可口的饭食。既有环境体面的正餐,也有美味便捷的快餐,而且基本上中餐、西餐、韩餐……各种风味齐全,非常方便。到中关村就不一样了,往往要把搜索半径扩大到一公里、两公里,甚至五公里,即便如此,有时候还是找不到“正确答案”。
难免怀念在东边的饮食生活。直到有天,看到一家重庆小面的店名似曾相识,进去一问,果然是从双井搬迁过来的,一试味道居然还是老样子,很快,这里就成了我与鹅厂同事的食堂。

刚刚入职腾讯时,内网的页面上,点赞最多的评论是:“莫非陈老师是行政部调来改善我司伙食的?”
记得说老实话,我哪有这个水平。不过在吃东西方面,优越感不敢说,自信倒还是有一点儿的,毕竟鹅厂周遭可口的店子少而又少。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就难免吹几句牛,普及一些关于食物的知识,比方说:“如何吃好一碗豌杂面?”
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常见到的情形是:在一碗普通的、来自重庆的条状面食跟前,小伙伴们首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狐疑。点东西时,三分之一的人要求免辣,三分之一会要奇奇怪怪的浇头,剩下的几位即便要了重庆小面的豪华版——豌杂面,也是吃相十分窘迫,最关键的,要了干熘(无汤豌杂)的两位,面全部吃完了,臊子还几乎完整地留在碗底。吃吧,有点儿咸。不吃,又觉得可惜。总之,人和碗都很无辜的样子。相信重庆人民要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愤怒地发来照会的。
重庆人吃小面,不像我的同事这样猴急,尤其豌杂面,要气定神闲,先用温柔的眼神向庄严覆盖着杂酱和耙豌豆的这碗面深情告别——我说得夸张了,应该说是认真检查一下臊子的分量和面的成熟度。然后,慢慢拿起筷箸,轻轻从右前方插入碗的底部,拇指、食指和中指用力,以筷尖为轴轻轻上挑。
对一碗干熘而言,外层和内部的温度是不同的,如果自上而下直接吃,开始面的硬度是合适的,而埋在下面的面条,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温度,会致使面体膨胀,甚至板结。如此轻挑数次,不仅让整碗面的温度趋于均匀,面条不至于粘连,也使“帽子” 均匀地包裹在每一根面条的四周。
一手托碗,一手举筷,咸淡一致地蘸匀调料
几经这样自下而上的翻动,直到豌豆、肉碎、榨菜末等等佐料也逐渐聚在最靠自己的位置,才可以正式吃面。,一口面,既有面香,也有肉质香,既有耙豌豆的绵沙,又有榨菜碎末细小跳动的爽脆,口味和牙感,如同一个弦乐四重奏现场,齐整、默契,层次分明又相互衬托。面之将尽,豌杂也刚好耗光。完美。
豌杂面是重庆小面中,我最热爱的品种。在重庆,每一家小面馆,面的软硬、肉臊的多少,都有不同,但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它的唯一性体现在这一坨金黄色的耙豌豆上。
“耙”,四川方言中用来形容绵软的字。耙豌豆也就是煮烂的豌豆,是川渝百姓的日常食物。成都人性格温婉,喜欢把豌豆煮到近乎无形,即便自己懒得煮,菜市场也买得到成品。做蔬菜汤、酥肉汤、肥肠汤,丢一勺耙豌豆,风味立刻不同。重庆人耿直得多,好的耙豌豆讲究软烂沙瓤而外形完整,尤其豌杂面更是如此。
耙豌豆这种价格极其便宜的食材,最初的出现,只是为了给分量不够的肉臊鱼目混珠地“撑场面”,所谓肉不够,豌豆凑。现在生活好了,肉也足够,人们非但没有把它从杂酱中剔除,反倒钟情于豌豆熟烂后美妙的口感和豆类加油脂的清香,它甚至成为山城早餐味觉的标识之一。
被豌杂面培育过味蕾记忆的人百爪挠肠
英国作家扶霞曾经在成都留学,回到英伦也自然多了不少川渝之地的朋友。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海外的中国学子们,对豌杂面可谓日思夜想。这些年在伦敦,川菜餐厅已经不少,有些做得已然十分正宗。但这些餐厅中,有豌杂面的却不多,原因是英国不容易买到白豌豆,这是耙豌豆的原料。,买吧,没有白豌豆,带吧,这种廉价之物,白白占用了行李箱的重量,又有些不甘心。
但很快,这个世纪难题就被解决了。一位留学生在超市里买了一罐胡姆斯酱,用郫县豆瓣加葱花煸了肉臊和榨菜,淋在了加热的胡姆斯酱上,奇迹出现了:一碗英伦风豌杂面在八千公里之外就此诞生,而且味道与重庆的近似度大于百分之九十五。甚至所有品尝的人都以为那就是耙豌豆,还有人抱怨:“你啷个把豌豆煮得愣么稀烂!”
胡姆斯酱又称鹰嘴豆泥酱,是一种源自中东的蘸酱,主要由鹰嘴豆、柠檬汁、蒜泥、橄榄油和芝麻酱组成。自13世纪起,胡姆斯酱就出现在埃及的烹饪书中,在中东和近东地区,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和世界,但胡姆斯酱却成了他们共同接纳的食物语言。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平时涂抹在面饼或者吐司上的酱料,被中国人当成了面条伴侣。
上面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姊妹篇。有个朋友在成都有两个圈子:一个是中国人的圈子,一个是外国朋友的圈子。在后一个圈子中,有一位原籍中东的朋友,经常在感叹四川美食的美味之后,非常无助地开始怀念家乡的胡姆斯酱。成都是一个拥有食物自信的城市,胡姆斯酱并不好买,怎么办呢?朋友把这位中东友人带到了菜市场,指着白豌豆说:“你不妨试一试这个,再加上一勺芝麻酱,你的故乡就回来了。什么?没有橄榄油哈,你可以试试用生的菜籽油替代啊。”

△《风犬少年的天空》剧照
食物是最亲善的使者
当然,这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同科不同属的两种豆子的果实,跨越万里,在不同的地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巧用,却这样水到渠成地达成了某种味觉上的默契。美食家们常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019年4月3日
于勒叔叔的生蚝
并不是对所有食物的最初体验都源于口腔。
初中有篇课文《我的叔叔于勒》,莫泊桑的。主人公的大龄二姐,好不容易找到对象,于是一家人决定去哲尔赛岛旅行。游船上,父亲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漂亮太太吃牡蛎——我对牡蛎这种食物的认知或者想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两位太太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以免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牡蛎的汁水吸进去……”
这个片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语文老师的肥东口音乡土气息浓厚,但身处内陆平原的我仍然觉得:第一,吃牡蛎这件事很高雅;第二,牡蛎这种海鲜应该很美味。
二十年前,去法国拍片,同行的导演老杨是重庆人,长着“不吃米饭要死”的中国胃,走到哪里都要找中餐。而翻译小宋在巴黎生活过,不时推荐我们尝尝法国饭。三人行,众口难调。直到有一天,小宋说:“我们今天去吃牡蛎吧。”我和老杨异口同声问:“是《我的叔叔于勒》里写的那种吗?”
我怎么觉得,这东西有点儿像我们说的生蚝或者海蛎子啊
马路边一家餐厅,墙上扯出来巨大的遮阳伞(同事告诉我这种餐厅叫brasserie,意思是小酒馆),我们正经八百坐等牡蛎上来。现实总是骨感,没有像于勒叔叔一样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它们赤裸着,集合在侍应生的托盘上出现了。这一刻,我有点疑惑,忙问:“?”小宋的回答非常决绝:“它们压根就是一种东西!”
我说这个“相见不如怀念”的故事,是想表达,一个吃货的养成,其实要经历无数次类似乌龙的尴尬。
是的,牡蛎就是生蚝,在全世界温度合适的海边都有生长。全世界对牡蛎的认识也有共通之处。首先,在很长的时间里,人类都认为此物催情。中国人认为它“形以壮阳补肾”,希腊人的爱神索性就是从牡蛎壳里诞生的。其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享用牡蛎的最好时节是秋冬两季。西方人甚至规定,单词里没有R的月份不吃此物(南半球除外),因为5月到8月,正值繁殖期,生蚝身心俱疲,且体内分泌一种酸,不好吃——这与中国人对水产的时令选择也一致。
中国以蚝入菜,可以煲汤,可以抱蛋,潮州蚝烙、闽南蚵仔煎、胶东炸蛎黄、大连炖豆腐
然而,在吃蚝的方法上,东西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但一定是做熟了吃,这应该是传统。尤其南方的烹饪,和生蚝同时料理的几乎还少不了荤油,比如蚝烙,视觉上已经肥美多汁的蛎肉,裹着芋粉煎,再一勺烧滚的猪油淋下去,登时腴香氤氲,动物性毕现。

西餐中牡蛎也用黄油或奶酪焗烤,但最常见的是生吃,最多配上柠檬、甜辣酱或者红酒醋,还属于选项。生蚝极难保存,因此可贵之处就在新鲜,生吃应该是对它最好的尊重。
坚硬的外壳包裹着柔弱的蚝肉,挑落一颗,灵动跳脱,接近百分之九十的鲜美汁液滑落食道的刹那,眼睛都睁不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顺滑中不失锋利的味觉体验,比如英、德就少有蚝客。电影里,憨豆把海鲜拼盘中的号称牡蛎中劳斯莱斯的特级吉拉多生蚝弃如敝屣,看得我真心疼。
我好吃不求甚解,偶尔会参加所谓的“土蚝”聚餐,桌上罗列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蚝种,淡的重的口味一路吃过去,甚至有不用签证便环游世界的幻觉。在座都是美食行家兼地理老师,熟稔各种牡蛎的味型口感以及出产地。我真记不住这么多外国名字,如果说真爱,我比较中意原产日本、现在更多生长在美国西海岸的熊本蚝,猫爪子一样,小小的,呆萌呆萌,弹性好,回口有水果味。
但我的朋友严肃地告诉我,熊本是入门级的,应该试试喜欢大牌的贝隆铜蚝,或者爱尔兰高威也比较有个性……对于一个三十岁才搞清楚生蚝就是牡蛎别名的人,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熊本生蚝
对美食的追求,对体面生活的向往,都源自人的本能,这是常识。
不过我还是决定继续在“蚝门”打打酱油,因为生蚝的美味和生活的美好。正如现在,我很难回忆起《我的叔叔于勒》是不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却清晰记住了吃牡蛎的场景一样。
2015年3月17日
所谓美食,
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
农历腊月二十九的首都机场,一眼望去,满是期待回家团聚的脸庞,而我刚和家人告别准备出差。
已经不记得这是我第几个春节没在家过了。新年是食物汇聚的高峰,拍摄与美食有关的纪录片,这是最“出活儿”的关口。所以这些年,一俟佳节临近,我和工作同伴就会整理行装,踏上征程。
这么说,其实没有一丁点儿抱怨或者诉苦的意思。都市里的农历新年,味道越来越淡,春节这种农耕社会盘点收成、休养生息的遗存,现今只能到山海之间去感受。此刻的我充满期待,不知道等待我的是哪一种美味。
赶到皖南的小山村已是深夜。看了张平导演和摄制组几天来拍摄皖南火腿的影像素材,心里踏实了很多。汪姐叫汪兆慧,是这次拍摄的主人公,春节前,她和丈夫备好了年货,还精心腌制了两条火腿,这与几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庆祝新年的方式如出一辙。这是只有在现代文明影响力覆盖减弱的偏远地区,能够遇见的景象。
第二天一早,踩着深巷中鞭炮的碎屑,穿过阴冷的雾霭,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宗祠——叶家祠堂,这里曾经是电影《菊豆》的拍摄地,旁边一座两百多年的院子就是汪姐的家。年三十,我们的拍摄还会在这里继续,要记录汪姐一家的团圆饭。

△《菊豆》剧照
汪姐十几岁嫁到叶家,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这些年她见的摄制组很多,当初张平导演为了皖南火腿过来村里踩点,很多人家都以过年太忙为托词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开民宿的汪姐看到了我们的万般无奈,心一软接纳了我们。她是村里公认的勤快人。“只要年夜饭能让我们团圆,其他的你们愿意拍就拍吧。”汪姐话里的意思是,除夕对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刻。
白天的拍摄准备十分顺利,我还是有点担心同事们的晚餐,尽管大家都说一碗泡面足矣,但大过年的……我决定努力一下。网上信息显示,这一天方圆几十里没有开张的餐厅。我只好打开通讯录,准备找朋友“下手”,并且聚焦到三个人身上:美食顾问周墙、名厨叶新伟和好友寒玉,从距离上看,寒玉在碧山村的民宿“猪栏酒吧”最近,先给她发微信,把前因后果简单说了。
寒玉还没有回微信,门外却响起一个女声:“请问陈晓卿可在?”我从楼上看下去,这不是叶静吗?叶老师是我在北京的好友,十多年前的一次徽州之行,让我感受到这里的安静和美好,安徽同乡叶静在北京听了我的描述十分心动,便决定和朋友一起去皖南买一个老宅。但我不知道,老宅居然就在汪姐家的旁边!接到寒玉电话,她立即过来找我。“不耽误你拍摄,晚上去我家过年三十哦,寒玉也来。”叶静做电影出身,特别利索,说完就回去准备了。
美食真是一个特殊行业,外表光鲜,实际上甘苦自知。就像我,朋友们在微信和微博上,感觉我每天就是吃吃吃。其实吃什么自然很重要,但更多的时候,我更喜欢和能说得来的人一起吃: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利益诉求,甚至没有主动拉关系、交朋友的欲望。
然而拍摄美食纪录片让我的饮食节律非常混乱,有时候会一日多餐,我曾经一天吃过六顿“正餐”,也曾经一顿吃过五十七道菜,发自内心说,这都是很累的事情。当然,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也有连续三四天盒饭的经历,饿肚子拍摄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所以能接到这样的邀请,我自然非常感动。
尤其是年三十,谁家不吃个团圆饭呢?谁家在这个时刻还会接待莫名其妙的一堆客人?只能是关系特别好的密友。那天晚上,摄制组七个人来到了叶静家,饭菜都已准备好,寒玉拿来了儿子做的精酿,叶静从北京背了一只内蒙古的羊,只加了盐,炖了一天,摄影师大飞是呼伦贝尔人,刚喝了一口羊汤就直呼“卧槽卧槽到家了”。
那一天,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全剧组的人都过了新年,摄制组和寒玉也都像叶静的临时家庭成员,特别开心。
吃了团圆饭,我捧着酒杯,心里想,世界上最好吃的果然是人。
潮州,大年初一一早,我们汽车、高铁、飞机,才到了潮州。到潮州的时候又是一个夜晚了,和之前一样,看片,讨论,第二天早上上山拍摄,因为是年初二,导演老费天不亮拎着一包饼干交给我,提醒说,今天我们可能没饭哦。
一直陪同摄制组做田野调查和拍摄的汕头美食家林珂却笃定地说,想想办法,饭还是有的。
要知道,我们拍摄所在的五址村离标准意义上有商业的集镇还有十多公里,村委会主任说尽可能地给我们安排一顿饭。导演和摄影师忙碌地拍摄。
由于今年气候太暖,五址村的茶山上,茶叶提前到了采摘的季节。茶农们无心过年,都在山上忙碌,梯田上经常能看到一家老小都在忙碌。大人们在采茶,老人带着孩子用土块砌好了一个小小的土窑,燃上火,把玉米、红薯,和腌好的整只鸡放进去。孩子们开心地把土窑压塌,让火的余烬把食物炊熟。
我在一边看着,心里想的是另一个摄制组在安第斯山拍摄的Pacha Manka,古印加人的大地之锅和我眼前看到的是那样地相同,只不过我们放的是鸡,而他们用的是豚鼠。
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饮食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
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
我和助手决定在林珂的带领下先去吃饭的地方一探究竟。这家没有名字的餐厅只有一张桌子,就在村口,然而餐厅老板一家正在享用午餐,老板娘一摊手,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潮汕话,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看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说到故乡,说到故乡的食物,这是人和人之间非常好的沟通媒介
老板娘叫曾德艳,是四川宜宾人,不过连林珂这样的潮汕土著都听不出来她的口音,她已经是一个地道的潮汕媳妇了。于是我开始用我拿不出手的四川话和她套磁,说到了黄金芽菜、大刀白肉、竹笋竹荪、姜鸭面,老板娘脸上才绽出笑容,害羞地说,你讲的这些要我妈妈才会做。显然,刚才的冷漠渐渐化解,老板娘决定给我们做一餐饭。。

△《风味人间》剧照
我非常理解老板一家此刻的心情,原本年初二是潮汕人回娘家的日子,她的母亲在韶关,和弟弟一起生活,原计划她们是要开车五个小时去韶关,趁着高速路免费,由于我们的到来,这个计划只好搁置了。
老板娘在摄制组到来之前,从邻居家买了一只水鸭炖上,打了边炉,然后又把二姐家春节做的一只白切鸡拆了,摄制组风尘仆仆出现的时候,菜已经摆满了一桌,而我和林珂已经喝了好几泡岭头单丛。
拍摄纪录片的人就像行脚僧,镜头前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让一顿饭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再回来看,饭做得有好有坏,只有当你饥饿的时候,饭才变得更加香甜。
吉林敦化,牡丹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新民村就在江边。初十那天从延吉机场出来,对面一个敦实的、穿着呢子大衣的男人跟我说,陈老师,我是择授,杨波让我送您去新民村。
择授陪着我在市里简单吃了口饭,外面突然开始下雪了。到新民村大概三个小时的路,开车的择授说,看起来今天我们到不了村里了。雪越下越大,好几次我都想着要不要返程,择授拍着方向盘说,你要相信我的驾驶技术。择授从前看过我的纪录片,也为敦化的杀猪菜能够被我们拍到而自豪。雪越下越大,摄制组为了安全回到靠近公路的一个小镇上等我,晚上我们就在镇上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
这里的团年是以村庄为单位,杀猪,办席,都需要很多家人过来帮忙
第二天天不亮,又经历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艰难地到达了摄制组所在的小村子,眼前的一切让我非常吃惊。目所能及处荒无人烟,只有几家房顶的烟囱冒着炊烟,一切安静极了。我天生怕冷,前一天在供销社买了棉裤,但很快就吹透了。和内地不同,。主人公老刘家杀了一头三百斤的大猪,我第一次明白了过去我们在城里吃到的杀猪菜实际上是不能称作杀猪菜的。用科学家的说法是,猪肉在最初的五个小时风味最为饱满,只需要白水煮一煮就有别样的甜香。
和全中国一样,全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春节对他们来说,和传统意义上的欢聚已经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好在东北人骨子里喜欢热闹,从初期开始,村子的秧歌队每天排练,也每天聚餐,在摄制组导演的眼里,各家各户的菜,差异非常小,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这种一个自然村落依赖美食聚集起来的力量,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现在最后的乡村中国的新年景象。
这里我只是把个人的春节行程做了一个梳理,其实从元旦开始,到6月30 日,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几个摄制组之间来回奔波。六个月,在北京安定地待着的时间不超过二十五天。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辛苦,就像春节,可以选择在家团圆,同样也可以看一看中国农业社会最后的样貌。我们过节的年味儿在一天一天变淡,而只有在平时我们无法看到的乡村里才能感受这种农耕文明遗留的强大传统,更何况在这一路上,有这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巧手又创造出这么多美好的食物。
八个月后,《风味人间》开播的那天,汪兆慧、林珂和择授都给我发来了短信,我和他们相隔万里,半年前的相逢在这时候重新让我感觉到了温暖。
用我朋友老六的名言:你带来欢笑,我有幸得到。
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
我的感恩之情是延续在我的工作里的,
2018年12月31日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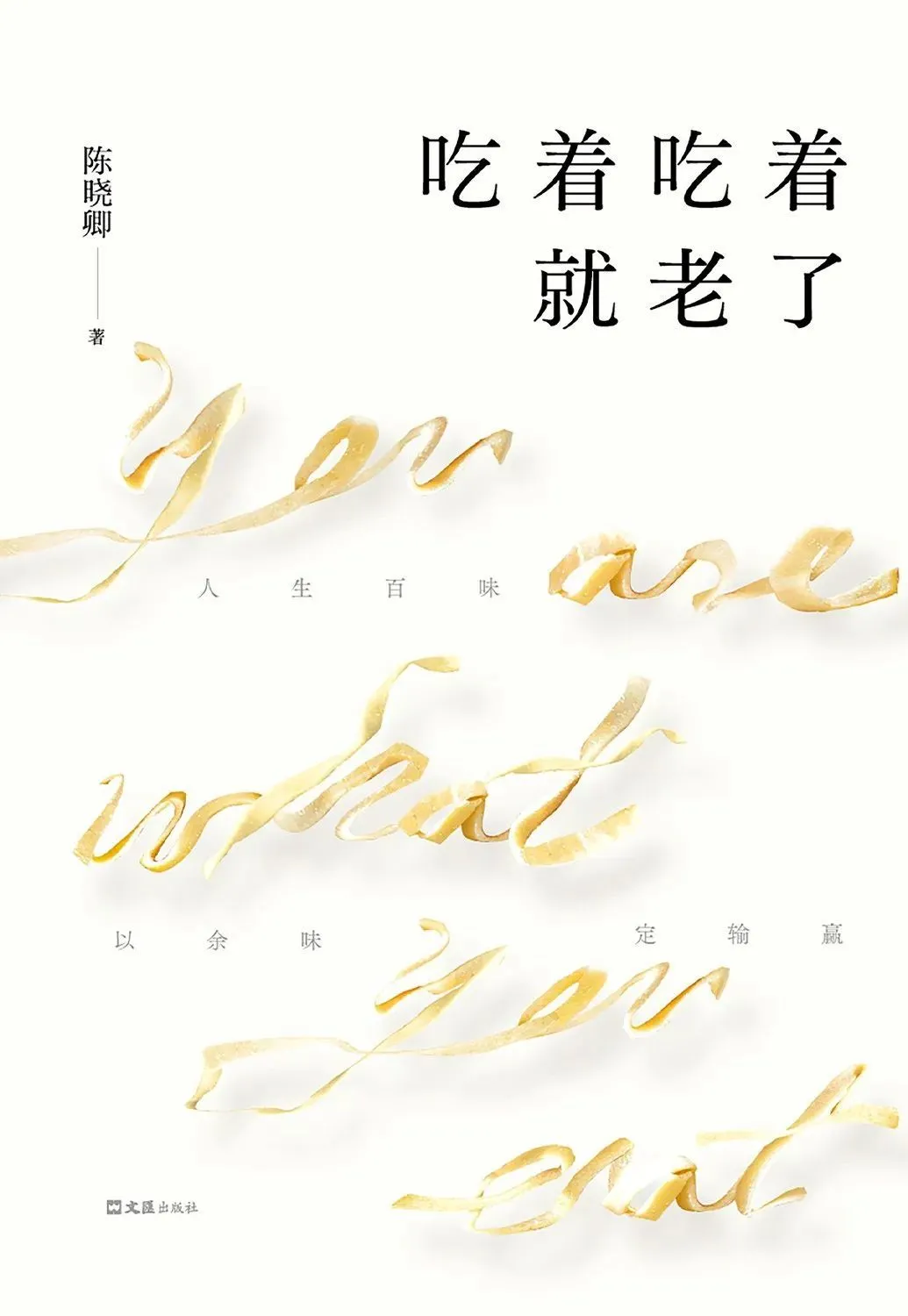
《吃着吃着就老了》
作者: 陈晓卿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 2024-1



